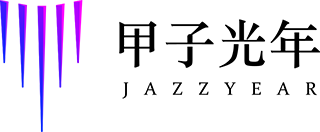《人物》2019年在报道《梁宁:中关村的妞儿》的开篇,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群独角兽创始人正在为复盘一次商业失败而吵架,谁也不服谁:
快的打车创始人陈伟星站在最后一排,拍着桌子大声说,「航叔我非常爱你,但是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因为你的观点太自我了。」对面的周航沉着脸,这个创立易到的独角兽扭过头,「他这个人逻辑不清楚,反正我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台下坐着的集团顾问、阿里高管都提了意见。哈佛回国的精英试图劝和,努力了一会儿也放弃了,「你们俩都把我说糊涂了,我这该听谁的?」
最后,一个女人站了出来,终结了这场争吵。她是整个会议室里个头最矮的,也是上头条次数最少的,仔细比较下来,她身上所捆绑的估值可能也是数字最小的。然而,当她站出来,房间里所有人突然都不说话了。她开始在白板上画图,分析这场争吵的重要节点,10分钟之后,争论结束了。
这位让一群独角兽创始人快速结束争吵的女人叫梁宁。
你很难用某个单一标签定义这位“带宽”很宽的女人:著名产品人、得到App课程《产品思维30讲》主理人、湖畔大学产品模块学术主任、百度顾问,曾任联想、腾讯高管,工作经历横跨BAT,与京东、美团、小米、华为等企业有长期深度交流。
她不从属于其中任何一家公司,却总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关乎巨头战略的闭门会议。这是个商业世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海啸般的信息噪音中,拥有清晰的分析系统和独立的思考框架,是一种极其稀缺的“熵减”能力。也是这种能力,让梁宁成为雷军口中的“中关村第一才女”,和大佬们总要定期会一会的特殊朋友。
今天的对话走进梁宁,谈谈这个时代你我最关心的问题。
1.谈思考:内部视角往往信息过载,信息过载就抓不住要点甲小姐:我听过很多你的课,你对很多企业总能建立敏锐简练的分析框架,这是如何做到的?
梁宁:我见过很多企业,发现一个特点,每当我和企业内部的人交流,员工和中层对自己的企业评价都会很低,都会觉得“我们公司不行”“你都不知道有多乱”“领导不行”“老板没有战略”......反正就是各种不行。如果你上脉脉读读论坛发言,会感觉所有公司都烂透了。
有道判断题,“我比别人更了解自己”,这句话对不对?你会比别人拥有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但是拥有信息和做出正确判断是两件事。你知道自己无数琐碎信息,但是关于你自己的几个核心判断,却未必能做得出。
一个人在公司是不是比外人更了解自己的公司?依然如此——内部的人往往会信息过载,信息过载就抓不住要点。人总会抓住自己感受强的那个点无限放大。所以,能拿住腾讯过去10年股票的,往往不是腾讯内部的人。
甲小姐:作为“局外人”,你怎么抓要点?
梁宁:我一直致力于用更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一件事。努力去建立框架放置信息,以及努力去找什么是核心。比如所有企业都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空间和竞争力。比如微信2012年推出时,这是个很大的空间,移动互联网刚刚开始,而腾讯在此有无敌竞争力。
甲小姐:你总能把一件事物的底层方法论、结构图、思维框架系统拎出来——这个能力很多人都很渴望,但做不到。
梁宁:因为我学的是系统设计,这跟本科专业直接挂钩。
我曾和一个组织竞选的人交流,他跟我讲,做竞选其实就是拉人头、做地推。他们把全部人口分成一个个格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规模效应单元”,然后分成4类:政治、教育、医疗、工商。一类一类,每天去盘。我当时很吃惊,以我以前狭窄的认知力,因为自己身处工商,更具体其实是“商”,总觉得工商是这个世界的80%,但在社会治理者来看工商其实是个很小的section。工商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最低的,一位中学校长或者一位医院院长的动员能力远高于一个公司老板。
其实,这个“极简社会模型”的背后就是一个“极简人生模型”。医疗是生死、肉体,教育是灵魂,工商是外部资源的配置、流通、增值,政治是公共空间。其实人生就是身体、灵魂、外部资源、公共空间,就这么点事。
再往前一点,我14岁开始学《周易》,《周易》比这个模型更复杂,极简社会模型分4类,周易分64类,周文王在三千年前概括的社会模型到今天依然是完整的。
甲小姐:你用什么模型理解当下的商业世界?
梁宁:一个坐标系:左边是“模糊”,右边是“精准”,上面是“规模效应”,下面是“反规模效应”。
比如中医是模糊的、反规模效应的,西医是精准的、规模效应的。越精准,知识的传递性才越清晰。模糊的好处是不易被推翻,但它不善于解决问题,你得“悟”。
艺术是模糊的、反规模效应的,正因为艺术是模糊表达,才给了读者更多想象空间,比如梵高在画里去掉了明暗概念。再比如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他是精准和反规模效应的,他认了“我这辈子就一个小店、10张桌子”的命运,这也是个很棒的人生。但我是精准和规模效应的推崇者,我受的训练让我对精准和规模更有感觉、更具现代性。
甲小姐:最近很多人很慌,很多政策靴子接连落地,教育、地产、平台经济、数据安全……很多人感觉“找不着北”。你怎么理解最近的变化?
梁宁: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正义”?我感觉我们的正义是大局观。
总书记的讲话就是他的OKR,他把OKR贴出来,大家向他对齐。比如,今天社会稳定,中美博弈,肯定是大局,能为这方面有贡献的,在国内还是有空间的。当然,为了充分理解这个大局观,王小川说,人们不仅要读书,还要读报。
甲小姐:一种说法叫“一切不利于生娃的行业都危险了”,所以教育产业就变天了。
梁宁:这是一种解读,但不是最本质的解读。你看我刚才讲的极简社会模型,教育是塑造社会的最核心的力量,这不仅是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是对当下年轻人的意识形态管理。
我的专业是研究产品和价值创造。我有三个模块,价值与感知,价值与规模,价值与共识。很多初次创业的创业者遇到挫折,对自己提供的价值是否成立,别人对此的感知如何都很难把握。而高手比如美团啊、阿里、腾讯、字节等,他们不但提供价值,而且能够驾驭规模,提供价值和提供规模价值,是非常不同的能力。而最高和最难的,是价值与共识。比如,黄金的共识是人类3000年演进的结果,而铂金就未能获得这种共识,比特币的共识正在形成中。钻石如果没有成功缔造共识和管理共识,它就是一个矿物,用来打磨钻头。我们看到的所有股价起伏都是因为共识。
共识的管理是最高价值。
比如蒋介石统一中国,他依赖的共识是“一致抗日”,各个军阀不论内心对蒋介石看法如何,谁都无法挑战这个共识,所有人需要在这一共识下协同。抗战结束,共识瓦解了,然后蒋介石没有新的共识可以再统一所有人,就变成了利益勾兑,而可以利益勾兑的人是非常少的;而毛主席从30出头一直在做的就是管理共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为什么可以燎原?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是“打土豪分田地”,把英雄情怀和个人利益完美结合,之后一直到现在是“为人民服务”。
共识管理意味着社会动员能力,共识是不可触碰的。
甲小姐:过去大半年,我们看到政府取消了关于服务业占比要提高以及刺激第三产业发展的说法,而反复提及的是“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不能再下降了”,你怎么理解这些变化?
梁宁:疫情让整个地球停转了,唯一有正常生产秩序的就是中国。我们有如此完整的工业品类,可以保证向全世界交付,这让我们有了工业全球输出的国家机会,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化机会——如果你在太空看地球,其他地方全停了,只有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建立的工业优势不是基于14亿人口的消费,而是对整个地球70亿人口的供给能力。
这其中一个巨大的机会是开启中国的造车时代。汽车是工业之王,在整个社会消费中排第一。在传统汽车领域,核心发动机技术大都来自国外,但汽车电子化后,动力来源从发动机变成电动机,中国是可以拥有核心技术的。所以这不是几个企业的事,中国最优秀的人都值得加入。
另一个巨大的机会是服装产业。我认为这是100年来服装产业前所未有的机会窗口。2020年是中国服装的分水岭,也是世界服装的分水岭。
甲小姐:这个分水岭来自什么?
梁宁:去年7月我看到一个现象:网红店7月夏装还在上新。我突然意识到,服装产业要变天了。
以前传统服装要提前9个月开订货会、提前半年排产,夏装5月上新,8月就开始上秋装了,一个季节的服装一年才能迭代一次。但现在武汉有了“快反工厂”——我们可以像迭代网页一样迭代衣服的设计。
比如一个直播,下面留言说领口太大,好,投票,领口改小。设计定稿,三天时间全国采购面料辅料,一天时间运到武汉,一天时间整理,上午上线,下午出货,当晚进仓库,当晚发货,这就是中国速度。以前的工厂集群都在长三角珠三角,因为是出口逻辑,要离港口近,而现在快反工厂在武汉,因为武汉到中国每个大城市都是4个小时。
你知道在武汉的快反工厂,一件羽绒服从上线到做成多长时间吗?130秒。他们创建了“一单流”,每条产线25个工人,每人负责3~4个环节,读秒,超过三秒就报警,上厕所都得25人一起去上。这就是为什么到7月夏装还能上新。
7月上新,8月2次上新,9月3次上新,10月4次上新,一直到1月还在上新——过去一年迭代一次,现在一年迭代五次,那对市场的认识、对用户的理解其实就完全是两个物种了。我们刚才谈到竞争力,迭代速度快就是个很重要的竞争力。
2020年相比2019年,天猫服饰时尚潮流类货品GMV增长了91%。
甲小姐:我还以为疫情期间大家不用见人,就不买衣服。
梁宁:粗糙判断似乎该如此,但真去看用户就会发现不一样。我是个用户主义者。有两个小孩抢笛子,笛子该归谁?如果粗糙判断可以根据物权。但亚里士多德不会这样判断,他会让两个孩子都吹一下,吹得更好的孩子应该拥有这个笛子。产业最终是用户来选择的,谁能把用户服务的更好,用户就是谁的。这个91%的增长,除了供给侧效率提升外,也有用户需求的改变,现在的用户更拥抱新圈层、新品类、新风格,今年每棵小樱花树下都会有个穿汉服的姑娘。
所以今天我会看到很多品类的中国生意人到了其他国家没有对手?因为两个红利,一是我们的供应链,二是我们沉淀出千人千面的算法。中国是个过度竞争的市场,大家是斗兽场里磨练出来的能力。
再比如能源产业,习大大承诺碳中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是全人类的共识,美国再傲慢,也不能挑战共识。
你看太阳能光伏,中国用了10年时间拥有了世界上光伏技术的所有核心技术。从另一个角度看,能源属性就由煤和油的资源属性变成了光伏和风机的制造业属性——我们把能源变成了制造业,这就把能源变成了中国的长项。
石油再这样使用,再有40年就挖光了,我们有生之年有可能会看到一个没有石油的地球。制造业是中国优势,当我们把光伏发电彻底做好,我们西部的穷乡僻壤就成了能源供给地,那可以成为迪拜啊。到那时,中国可变成能源输出国,加上一带一路,真的很伟大。
现在我们再来看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你会发现,服务业从工业抢人抢得非常厉害,服务业对人的知识积累要求是低的,也容易舒适,像欧洲那些人端个咖啡,一辈子这么过去也是ok的,但工业对人是一直有学习挑战的——不引导的话,大家很容易选择服务业。但服务业只服务14亿中国人,但工业是可以出口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甲小姐:所以政策的指针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从更大维度看,是为新一轮全球化考虑?
梁宁:对。从国运角度,上天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有了工业全球输出的国家机会,如果最后由于工厂招不到人,年轻人都去服务业了,最后国家失去了这个机会,那是很遗憾的,所以国家当然要打压服务业、鼓励制造业。
甲小姐:国家打击互联网平台经济也是这个原因吗?
梁宁:这是另外一件事。鼓励制造业是效率问题,而打击互联网是公平问题。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基础设施私有化。欧洲和美国最富有的家族就是私人持有基础设施,但在我们国家,基础设施应该是公有的。互联网有了基础设施的特性,如果你垄断,还不创新,只是基于别人的生活做分配,这就是不公平,所以国家要反垄断。
甲小姐:国家去年开始把数据定为生产要素,是否拥有大量数据的平台要面临国有化?
梁宁:这涉及垄断和创新豁免的问题。反垄断法也有垄断的豁免情形,如果你必须拥有数据才能创新,而你的创新可以回馈社会,我相信国家会支持,可能会有创新豁免。
以前社会和市场是分开的,但今天,社会和市场的边界变模糊了。你在社会上的动作可能瞬间被市场惩罚,像吴亦凡;你也可能会瞬间被市场奖励,像鸿星尔克。
企业总想的是市场成本,但很多事也有社会成本。中国政府是无限责任的政府,企业是有限责任的企业,但当企业成为了社会重要的分配者,社会成本却没有记在企业的账上——社会成本我来扛,市场收益你来拿?那我不干。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以前的经济学没有覆盖的地带。
3.谈趋势:工业时代是力量的比拼,智能时代是知识的比拼甲小姐:前两天看你的博客,你提到最近福布斯中国发布的2021年最佳CEO榜单排名,雷军排第一,而互联网企业家没有一人上榜。你写道“英雄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个沉甸甸的、永久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的时代可能到了一个段落,到了一个分水岭。这个过程中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还来不及真正的认识它和理解它,就又可能被裹胁着到另外一个时代去了。”简言之,互联网的时代结束了?
梁宁:结束了。
甲小姐:下一个时代是?
梁宁:我觉得互联网只是个过渡时代。上一个时代是工业时代,核心是力量,更大规模、更精密的机械、能源;接着是互联网时代,核心是信息对齐,现在信息已经对齐了;接下来是智能时代,核心是知识——工业时代是力量的比拼,智能时代是知识的比拼。
当我们把人眼可以看到的一切都让机器看到,基于机器会产生新的知识。比如美团的城市大脑把经济数据、地图、餐馆整合起来,这是知识。有了知识,行动就像上帝视角;没有知识,行动就摸摸索索靠运气。
比如一个朋友买股票老买在山顶上,每次见我都抱怨。抱怨了3次我忍不住了,我说你总是归因为“运气”,为什么不归因为“知识”?你在一个地方打鱼,一次两次没捞着,这是运气,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持续4年没打到鱼,这是知识问题。你对这个地方有足够的知识吗?这里有鱼吗?什么鱼,生活在什么水层,有什么习惯特性?
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学知识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生活还是依赖本能。本能能带给你的就是被动响应。知识才能让你看到世界的轮廓,运转的规律,让你建立主动。那天一个硕士毕业的小姐姐把我气着了。我说她,你花了20年学习知识,却只靠本能生活。
甲小姐:18年4月,你曾写下一篇影响力很大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你在万字长文中感叹“为什么我们建的了房子,放的了卫星,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现在三年多过去了,硬科技成为政策中的大国重器,大量芯片公司涌现,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也出来了,你对待中国的芯片、操作系统和整个生态,此刻会更乐观吗?
梁宁:更乐观了。有的事是工程的事,有的事是创新的事,前者是看天花板,后者是看天。我们的体制擅长解决工程问题,当一件事已经成为工程,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今天被卡脖子,这是个看天花板的事,有作业可抄,哪怕全套工具链都被卡,可能一两年之内我们都可以解决。需要注意的还是我们对创新的持续激励。
甲小姐:你在上述文章中强调“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系统”,经过这几年,我们的生态能力有变化吗?
梁宁:有变化。原来的场景是PC场景,今天的场景是互联网、云计算,这是个特别大的变化。以前是windows场景,我们没有发育的机会,现在在云计算生态里,我们是完整的,会有很多新场景可以发育。所以我讲,苹果开始做芯片,英伟达的股票就可以抛了,为什么?因为苹果有完整生态,所有数据闭环都反映在自己的生态里,迭代速度一定是最快的。
甲小姐:你的思维模式应该很适合做基金,为什么不做?
梁宁:我在14、15年和两个朋友做过一个天使基金,但这件事让我很痛苦。我发现做天使投资99%的时间都是“在沙里淘金”,大量时间是无效的。我是个非常不善于处理情绪的人,尤其当对方情绪激动时,我很容易沾染上别人的情绪,又清洗不掉。我很怕被拒绝,也不愿意拒绝别人,但做投资90%的情况都是拒绝,这是交不了朋友的。这些都让我很痛苦,后来我觉得算了,我的判断能力可以在股市上挣挣钱,此外时间可以读读书,去和伟大的人对话。所以我后来就不工作了,一直到现在。
甲小姐:你很擅长用简单框架理解外界,你怎么理解自己?
梁宁:我不工作之后学了两年心理学,后来我明白了我无法工作的原因——当时我的心理结构已经无法支撑我再做任何事了。当时我的心理结构是:外壳是个女战士,内核是个巨婴。
人都有底层操作系统。我总是很容易开头,开完后就脆断,“啪”一下一摔到底,然后“啪”一下又开一个不错的头,有个不错的进展,然后“啪”一下又折掉,我之前的人生老是这样。在做事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浑然的,没有超越的视角来观察自己,只是疲于应对每天的事,后来我才明白,我的心理结构有问题。
我从小在部队家庭长大,父母只会用培养战士的方法来培养孩子。部队的价值系统和商业的价值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军人压制个人情感,你流露出恐惧就会被嫌弃。我从小怕疼、怕冷,这样的情绪一定会被父母打压或者嫌弃,所以我一直是压制自己的情绪的。
一个东西只有被讨论才会发展,但我从小就学会服从,内心活动在我家内部是不讨论的。我从小就不会讨论生活话题,他们都穿军装,住营房,所有东西全是配给的,我上了大学才第一次花钱。我刚创业的时候,那些人跟我聊中午吃什么,我就特别吃惊——吃饭难道也是话题吗?
人是被环境塑造的,所以我崇拜强者,特别害怕袒露软弱,也不会和任何人有真正亲密的关系。外在总是个很酷的女战士,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分,最难的留给我就行了”,但我的内在没有充分发育过——一个成熟人的弹性和灰度,我是没有的。所以我总有部分能力可以开得比别人漂亮,但我的心理素质又很差,应对挫折的能力很弱,也不能和人有弹性的连接,就很容易脆断。这是我对自己的理解。
后来我逐渐发现,“正确”其实是个非常粗糙的事情,但“好”是个特别细微的事情。
我学的是计算机,大三大四就在联想写代码,讨论问题都是画线框图。你可以很粗糙地写代码,但如果你要做一个页面让人很舒服,需要很多细微的东西。但这种细微的东西我没有。
我很难感知到别人的表情。比如我小时候看不懂电影,一个演员的表演,叠加场景,叠加音乐,我就感受不到。比如我在跟人沟通时,总会对“正确”有特别强的追求。我在联想20出头就被提成副总,当时开会,开着开着一个人突然推门出去了,过一会儿我问,他怎么上厕所还不回来?其他人告诉我,我已经把这人逼得没办法了,对方只是不愿意当众爆发,只能推门出去了——我意识不到,我还以为是他要上厕所。
有个朋友说我是“强行用智商拉高情商”,雷晓宇说我的反射弧“可以绕地球一圈,再打个蝴蝶结”。别人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和自由流动的,我总需要不断架构逻辑才能判断。我曾经问我一位朋友什么是爱?问了两年,问了他四五十遍,朋友觉得好痛苦,你干嘛呢?
后来我才逐渐理解,“正确”是多么粗糙,“好”又是多么细微,而且“好”往往没有“正确”可言——这就要抛掉以前的正确逻辑,重新建立新的逻辑。
我觉得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个人夸我“很敏感”。这真是后天习得的。
 38401
38401 2
2 2
2 0
0